当年,阿富汗裔的两兄弟阿雅恩(Ayan)和法汉(Farhan)分别才14和16岁,住在巴基斯坦奎达(Quetta)。和其他青年一样,他们到学校上课、踢足球、偶尔帮母亲跑腿办事。
由于有些药无法在他们的镇上买到,有一天,母亲吩咐他们到附近的小镇买点药。
不料,那一次的出行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
他们兄弟俩并不知道,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母亲,更不知道他们就此离开家乡,独自展开未知漫长的旅程,来到马来西亚。
这是他们的故事,由艾迪拉(Aidila Razak)采访。
我们出生之前,家乡阿富汗爆发内战。我的父亲是个农夫,当时,我的两个哥哥已出生。
我的父亲和叔叔是地主。内战爆发前,家乡闹出土地纠纷,有人抢夺我们的土地。父亲和叔叔挺身反抗,使他们开始在当地变得有影响力。
随着父亲越来越有影响力,内战开打时,有人开始针对他和我们一家。于是,我的父母和两个哥哥逃到巴基斯坦奎达市(Quetta)的哈扎拉镇(Hazara)。
在哈扎拉,我的父母又生了四个孩子。我(法汉)和阿雅恩(Ayan)排名第4、第5,没有任何身份证件。
奎达是蛮大的城市,而哈扎拉镇只占据奎达的一小部分。我们大部分时间只待在哈扎拉镇,很少离开。
哈扎拉镇的街道窄小,没有什么车子往来,小孩会在街上放风筝或玩弹珠。父亲过世前,我们有时候也会到他的服装店帮忙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都会去上学,或者在街上和朋友玩乐、踢足球。
那天,母亲要我们到附近的小镇买药。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帮母亲买药,但不一样的是,这一次遇上了路障。
警察充公我们的手机,带我们到警局待了两天,不允许我们联系家人。
第二天,他们让我们坐上一辆货车,什么也没说。当时夜已深,车上挤满了人。过了许久,我们才意识到,货车正在驶往阿富汗边境。
一路上,我们脑海中想的是母亲和家人。我们很担心母亲,她的两个儿子消失了两天,她会怎么想?
货车开到阿富汗边境后,他们就把我们留在那儿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踏足阿富汗的土地。当时也有其他人一起被遣返,但他们没有理会我们。我们不知所措,很害怕。
阿富汗边境有些店屋,我们身上还留着帮母亲买药的钱,于是,马上去买了电话和电话卡,打电话回家。
我们清楚记得母亲在电话那头叮嘱我们:“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家。”
她说,只要我们愿意付钱,有些人会帮我们,他们会送我们回去巴基斯坦。
边境处有家酒店,母亲叫我们到酒店去问问,找个可以带我们回去巴基斯坦的人。我们不知道可以相信谁,但已别无选择。
待在边境小镇的短短三天内,我们曾三度尝试跨越边境。
前两次我们按一般方式跨越边境,但没有成功。我们的中介原应跟边境守卫谈好,让我们入境,但每次关卡检查都非常严格。
那天晚上,天一片漆黑,我们只能循着月光前进。我们尾随着一名男子进入森林、穿过山丘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,只能跟着他走了好几个小时。
但是,边境守卫十分严格,我们始终无法入境。我们无法安全抵达巴基斯坦,无奈之下只好折返。
母亲认为,一旦父亲的敌人知道我们身在阿富汗,必定会来找我们,因此继续待在阿富汗是十分危险的事。她说:“想个办法离开阿富汗。”
移民澳洲的大哥想到一个办法:既然我们不能通过陆地跨境,何不尝试搭飞机?不过,我们必须先到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( Kabul )申请护照。当时,我们以为,有了护照,我们就可以申请签证,顺利飞到巴基斯坦。

喀布尔距离边境超过500公里。每每想起母亲说这趟旅程将充满凶险,我们就十分害怕,可是我们并无退路。
我们花了一星期就拿到护照,哥哥也汇了点钱给我们过日子。在经历了不确定的一周后,事情似乎开始好转。但是,我们并不知道申请签证和飞到巴基斯坦,其实是不可能的事。
当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紧张,两国之间没有航班飞行。我们决定无论如何先离开阿富汗,所以得飞到别的国家。
我们问了旅游中介,对方说,凭着阿富汗护照,我们只能申请到前往马来西亚的签证。我们对马来西亚一无所知,但哥哥说:“行,从马来西亚你可以再飞往其他国家。”我们也同意了。
当时,我们身无一物,只从喀布尔带了几件衣服,和哥哥汇给我们的钱。
飞往马来西亚的途中,我们其实毫无头绪。到底抵达后会发生什么事?谁会帮助我们?要如何和别人沟通?
到了吉隆坡国际机场,我们拿着签证,顺利通关。但是当机场的门打开时,我们吓了一跳——离开阿富汗前,那里还是冬天;但到了马来西亚,那里的天气却热得像有人朝我们扔了一把火。
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只好给帮我们订机票的旅游中介打了通电话。他教我们如何搭乘德士,然后请德士司机载我们到吉隆坡安邦。
中介说:“你们的人都聚在安邦。”但我们并不认识任何人。我们打算到安邦以后,再听听路上的人,谁会说波斯语(Persian)。
下午3点左右,我们到了安邦。德士司机把我们留在安邦坊(Ampang Point),路上的人不多,也没有听见任何人说波斯语。我们只好坐在路旁干等。
神奇的是,不久后就有一群男子走过,他们所说的便是波斯语。看见我们时,他们也停下了脚步。
他们问:“你们刚抵达马来西亚吗?有地方住吗?”没有。他们愿意助我们一把,还带我们到附近的小公寓。
和他们交谈后,我们才发现飞到澳洲和哥哥团聚并非易事。而且,我们也开始意识到,我们成了“难民”。
他们说,最好的办法是向联合国难民署求助和注册,难民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。
我们住在那间公寓将近两个月,大部分时候,其他人都会帮助我们。我们从不懂得烹煮,一开始只能靠吃快熟面过活,直到公寓里的年轻男子教我们怎么煮简单的料理。

联合国难民署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他们给我们发了难民卡——我们在巴基斯坦不曾有过证件。还没拿到难民卡之前,我们非常担心,因为我们仅有的签证即将到期。
后来,我们联系上马来西亚孩童之声福利协会(Suka),一个帮助难民孩童的非政府组织后,我们就搬离了安邦的公寓。Suka协会帮我们找到庇护所、领养我们的家庭和一间学校。
我们来马来西亚快两年了。每次跟别人说起我们的故事时,我都会这么形容“我们的经历就像人在海上漂浮一样,只能任由海浪牵引着。大部分时候你无法控制方向,但你必须不断往前、你必须坚强,不论海浪将你冲往何处,你都要坚持下去。
我们要有耐性、要坚强。若海浪把你漂到一座岛,你就在岛上生活。若浪潮带你到另一国家,那就在那个国家生活。适应那个国家,想办法活下去。
其实,我们算是幸运的,一开始有哥哥指引我们,然后是安邦公寓那屋子的同乡、帮我们进入状况的其他难民,接下来还有Suka协会。
有些难民来到马来西亚之后,根本无处可去,最终只能在公园溜达多个夜晚。之后,他们需要打工养活自己,即使他们还年幼。
不过,当我们年满18岁时,Suka协会不会再帮助我们。那似乎是很可怕的未来,但我们不会畏惧。所有事情都有时限,时机到了就是时候往前看。我们需要找到继续向前的办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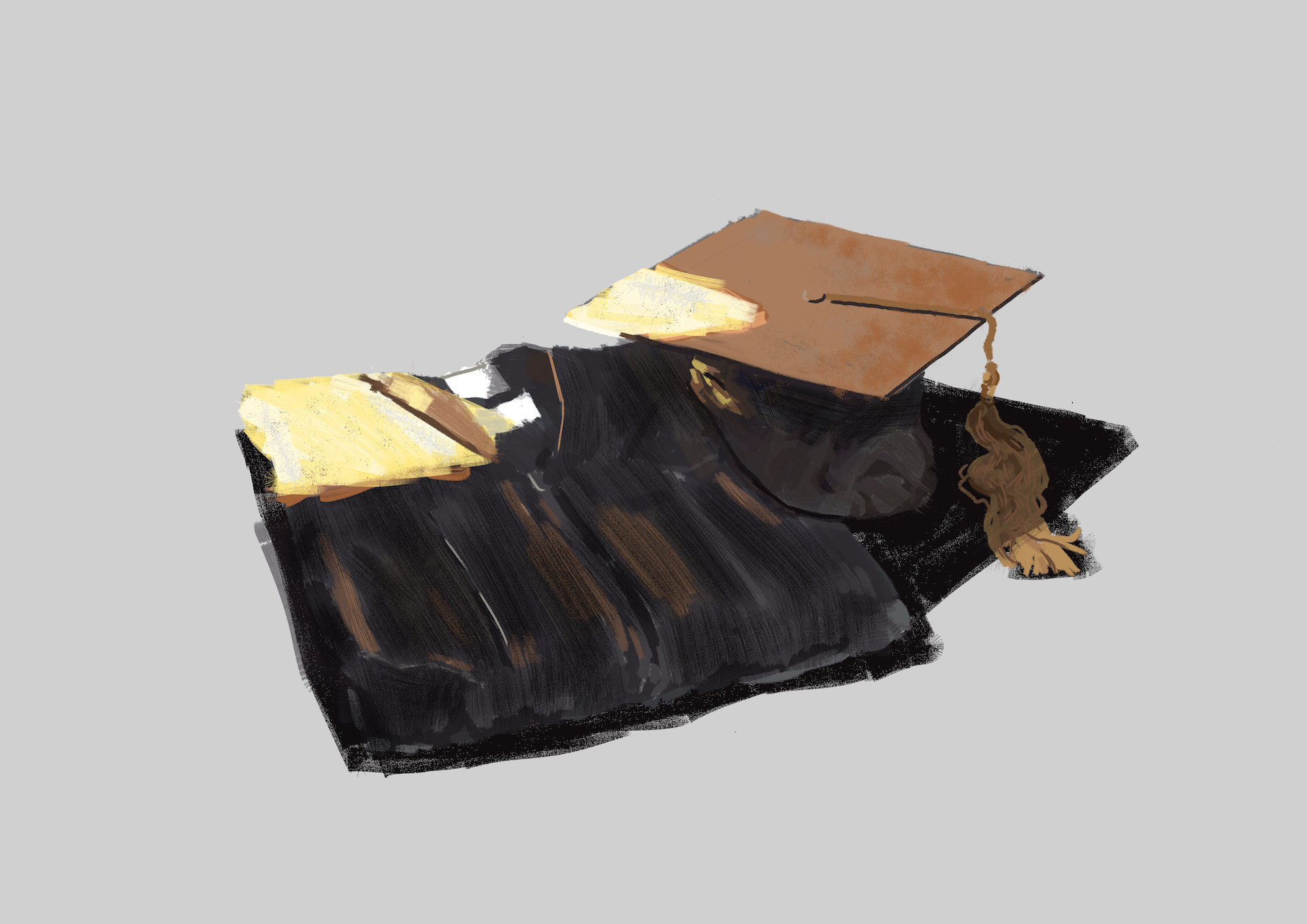
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到澳洲和哥哥相聚,但这由不得我们决定,而是联合国难民署和澳洲政府。所以,我们只能待在这里,读书、等待。
我们在难民学校上学。学校有四个老师,科目包括科学、数学和社会研究。学校教的不尽完善,但这是在艰难的时刻,我们所能得到的教育。
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,不管是在运动或学业方面,我们想要拥有成功的人生。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任何难民曾经考上大学,或许英国国际普通中学教育文凭(IGCSE)是难民可以到达的顶峰。
自从来到马来西亚,我发现本地人把难民视为异类,或许有些难民也这么看待马来西亚人,但他们都错了。
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异,我们其实是一样的,差别只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证件。




